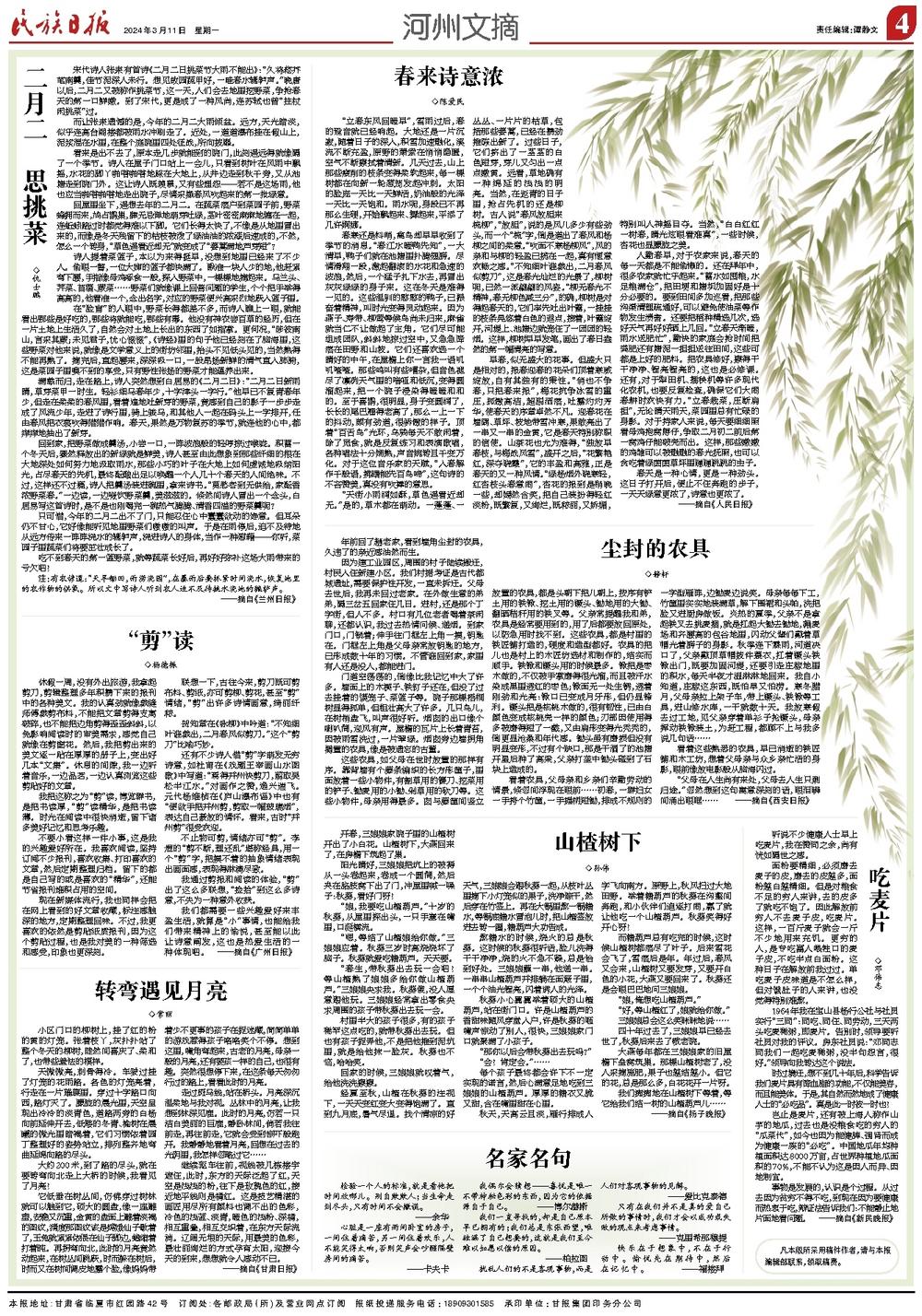◇静轩
年前回了趟老家,看到墙角尘封的农具,久违了的亲近感油然而生。
因为建工业园区,周围的村子陆续搬迁,村民入住新建小区。我们村据考证是古代都城遗址,需要保护性开发,一直未拆迁。父母去世后,我再未回过老家。在外做生意的弟弟,隔三岔五回家住几日。进村,还是那个丁字街,但人不多。村口有几位老者喝着茶闲聊,还都认识,我过去热情问候、递烟。到家门口,门锁着;伸手往门框左上角一摸,钥匙在。门框左上角是父母亲常放钥匙的地方,已形成数十年的习惯。不管谁回到家,家里有人还是没人,都能进门。
门道空荡荡的,倒像比我记忆中大了许多。墙面上的木楔子、铁钉子还在,但没了过去挂着的馍笼子、菜篮子等。院子那棵梧桐树显得孤单,但粗壮高大了许多。几只鸟儿,在树梢盘飞,叫声很好听。烟囱的出口像个喇叭筒,迎风有声。屋檐的瓦片上长着青苔,因被雨雪洗过,一片翠绿。烟囱旁边墙拐角搁置的农具,像是被遗忘的古董。
这些农具,如父母在世时放置的那样有序。靠背墙有个藤条编织的长方形筐子,里面放着一些小物件,有割草用的镰刀、挖菜用的铲子、锄麦用的小锄、剁草用的砍刀等。这些小物件,母亲用得最多。囱与藤筐间竖立放置的农具,都是头朝下把儿朝上,按序有铲土用的铁锨、挖土用的镢头、锄地用的大锄、翻晒秸秆用的铁叉等。父亲常提醒我和弟,农具是经常要用到的,用了后都要放回原处,以防急用时找不到。这些农具,都是村里的铁匠铺打造的,硬度和造型都好。农具的把儿也是村上的木匠坊选材和制作的,结实而顺手。铁锨和镢头用的时候最多。锨把是枣木做的,不仅被手掌磨得很光溜,而且被汗水染成黑里透红的枣色;锨面无一处生锈,透着刚劲和光亮:锨口已变成月牙形,但仍显锋利。镢头把是核桃木做的,很有韧性,已由白颜色变成核桃壳一样的颜色;刃部因使用得多被磨得短了一截,又由扁形变得光秃秃的,倒更显沧桑和年代感。锄头虽有磨损但没有明显变形,不过有个缺口,那是干涸了的池塘开垦后种了高粱,父亲打垄中锄头碰到了石块上造成的。
看着农具,父母亲和乡亲们辛勤劳动的情景,倏忽间浮现在眼前……初春,一群妇女一手挎个竹筐,一手握柄短锄,排成不规则的一字型雁阵,边锄麦边说笑。母亲每每下工,竹筐里实实地装满草,解下围裙和头帕,洗把脸又进厨房做饭。炎热的夏季,父亲不是拿起铁叉去挑麦捆,就是扛起大锄去锄地,碾麦场和齐腰高的包谷地里,闪动父辈们戴着草帽光着膀子的身影。秋季连下霖雨,河道决口了,父亲戴顶草帽披件蓑衣,扛着镢头铁锨出门,既要加固河堤,还要引走庄稼地里的积水,每天半夜才湿淋淋地回来。我自小知道,庄稼这东西,既怕旱又怕涝。寒冬腊月,父母亲拉上架子车,带上镢头、铁锨等工具,进山修水库,一干就数十天。我放寒假去过工地,见父亲穿着单衫子抡镢头,母亲挥动铁锨装土,为赶工程,都顾不上与我多说几句话……
看着这些熟悉的农具,早已消逝的铁匠铺和木工坊,想着父母亲与众乡亲忙活的身影,眼前像放电影般从脑海闪过。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忽然想到这句寓意深刻的话,眼泪瞬间涌出眼眶…… ——摘自《西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