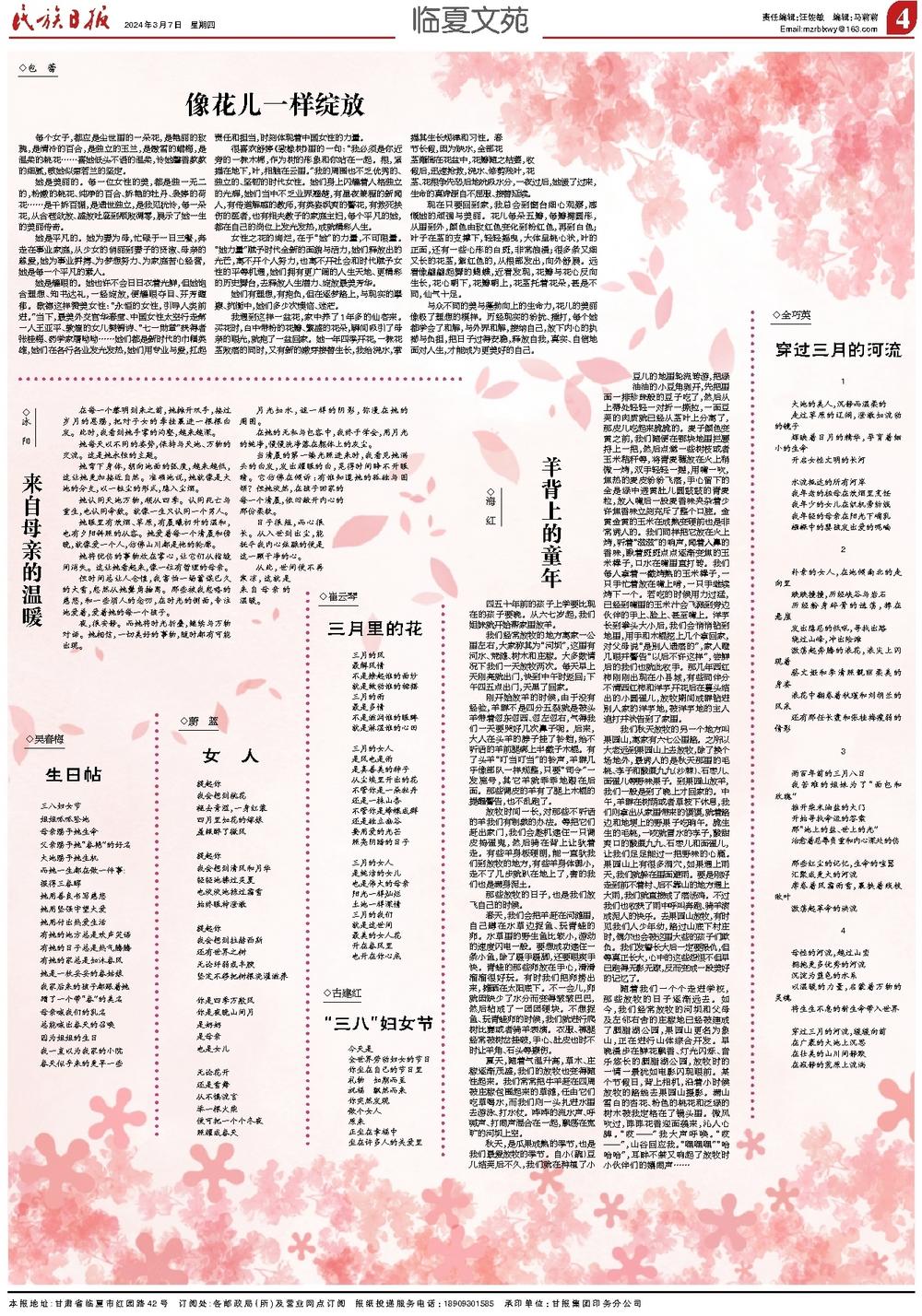四五十年前的孩子上学要比现在的孩子要晚。从六七岁起,我们姐妹就开始帮家里放羊。
我们经常放牧的地方离家一公里左右,大家称其为“河坝”,这里有河水、荒滩、树木和庄稼。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一天放牧两次。每天早上天刚亮就出门,快到中午时返回;下午四五点出门,天黑了回家。
刚开始放羊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羊群不是四分五裂就是被头羊带着忽东忽西、忽左忽右,气得我们一天要哭好几次鼻子呢。后来,大人在头羊的脖子挂了铃铛,给不听话的羊前腿绑上半截子木棍。有了头羊“叮当叮当”的铃声,羊群几乎像部队一样规整,只要“司令”一发施号,其它羊就乖乖地跟在后面。那些调皮的羊有了腿上木棍的提醒警告,也不乱跑了。
放牧时间一长,对那些不听话的羊我们有制裁的办法。等把它们赶出家门,我们会趁机逮住一只调皮捣蛋鬼,然后骑在背上让驮着走。有些羊身板硬朗,能一直驮我们到放牧的地方,有些羊身体弱小,走不了几步就趴在地上了,害的我们也是满身泥土。
那些放牧的日子,也是我们放飞自己的时候。
春天,我们会把羊赶在河滩里,自己蹲在水草边捉鱼、玩青蛙的卵。水草里的野生鱼比较小,游动的速度闪电一般。要想成功逮住一条小鱼,除了蹑手蹑脚,还要眼疾手快。青蛙的那些卵放在手心,滑滑溜溜很好玩。有时我们把卵捞出来,摊晒在太阳底下。不一会儿,卵就因缺少了水分而变得皱皱巴巴,然后粘成了一团团硬块。不想捉鱼、玩青蛙卵的时候,我们就进行爬树比赛或者骑羊表演。衣服、裤腿经常被树岔挂破,手心、肚皮也时不时让羊角、石头等擦伤。
夏天,随着气温升高,草木、庄稼逐渐茂盛,我们的放牧也变得随性起来。我们常常把牛羊赶在四周被庄稼包围起来的草滩,任由它们吃草喝水,而我们则一头扎进水里去游泳、打水仗。哗哗的流水声、呼喊声、打闹声混合在一起,飘荡在宽旷的河坝上空。
秋天,是瓜果成熟的季节,也是我们最爱放牧的季节。自小(豌)豆儿结荚后不久,我们就在种植了小豆儿的地里轮流转游,把绿油油的小豆角剥开,先把里面一排珍珠般的豆子吃了,然后从上蒂处轻轻一对折一撕拉,一面豆荚的肉质就已经从茎叶上分离了,那皮儿吃起来脆脆的。麦子颜色变黄之前,我们随便在哪块地里拦腰捋上一把,然后点燃一些树枝或者玉米秸秆等,将青麦穗放在火上稍微一烤,双手轻轻一搓,用嘴一吹,焦热的麦皮纷纷飞落,手心留下的全是绿中透黄肚儿圆鼓鼓的青麦粒,放入嘴后一股麦香味夹杂着少许焦香味立刻充斥了整个口腔。金黄金黄的玉米在成熟变硬前也是非常诱人的。我们同样把它放在火上烤,听着“滋滋”的响声,闻着入鼻的香味,瞅着斑斑点点逐渐变焦的玉米棒子,口水在嘴里直打转。我们每人拿着一截烤熟的玉米棒子,一只手忙着放在嘴上啃,一只手继续烤下一个。若吃的时候用力过猛,已经到嘴里的玉米汁会飞溅到旁边伙伴的手上、脸上、甚至嘴上。洋芋长到拳头大小后,我们会悄悄钻到地里,用手和木棍挖上几个拿回家,对父母说“是别人遗落的”,家人瞪几眼并警告“以后不许这样”,尝鲜后的我们也就此收手。那几年西红柿刚刚出现在小县城,有些同伴分不清西红柿和洋芋开花后在蔓头结出的小圆蛋儿,放牧期间成群钻进别人家的洋芋地,被洋芋地的主人追打并状告到了家里。
我们秋天放牧的另一个地方叫果园山,离家有六七公里路。之所以大老远到果园山上去放牧,除了换个场地外,最诱人的是秋天那里的毛桃、李子和酸蔴九九(沙棘)、石枣儿、面蛋儿等野味果子。到果园山放羊,我们一般是到了晚上才回家的。中午,羊群在树荫或者草坡下休息,我们则拿出从家里带来的馍馍,就着路边和地埂上的野果子吃晌午。脆生生的毛桃,一咬就冒水的李子,酸甜爽口的酸蔴九九、石枣儿和面蛋儿,让我们足足能过一把野味的心瘾。果园山上有很多洞穴,如果遇上雨天,我们就躲在里面避雨。要是刚好走到前不着村、后不靠山的地方遇上大雨,我们就直接成了落汤鸡。不过我们也收获了雨中呼叫奔跑、骑羊滚成泥人的快乐。去果园山放牧,有时见我们人少年幼,路过山底下村庄时,偶尔也会被这里大些的孩子们欺负。我们发誓长大后一定要报仇,但等真正长大,心中的这些怨恨不但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反而变成一段美好的记忆了。
随着我们一个个走进学校,那些放牧的日子逐渐远去。如今,我们经常放牧的河坝和父母及左邻右舍的庄稼地已经被建成了胭脂湖公园,果园山更名为象山,正在进行山体综合开发。早晚漫步在鲜花飘香、灯光闪烁、音乐悠长的胭脂湖公园,放牧时的一情一景犹如电影闪现眼前。某个节假日,背上相机,沿着小时候放牧的路线去果园山摄影。满山雪白的杏花、粉色的桃花和泛绿的树木被我定格在了镜头里。微风吹过,阵阵花香迎面袭来,沁人心脾。“哎——”我大声呼唤。“哎——”,山谷回应我。“嘿嘿嘿”“哈哈哈”,耳畔不禁又响起了放牧时小伙伴们的嬉闹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