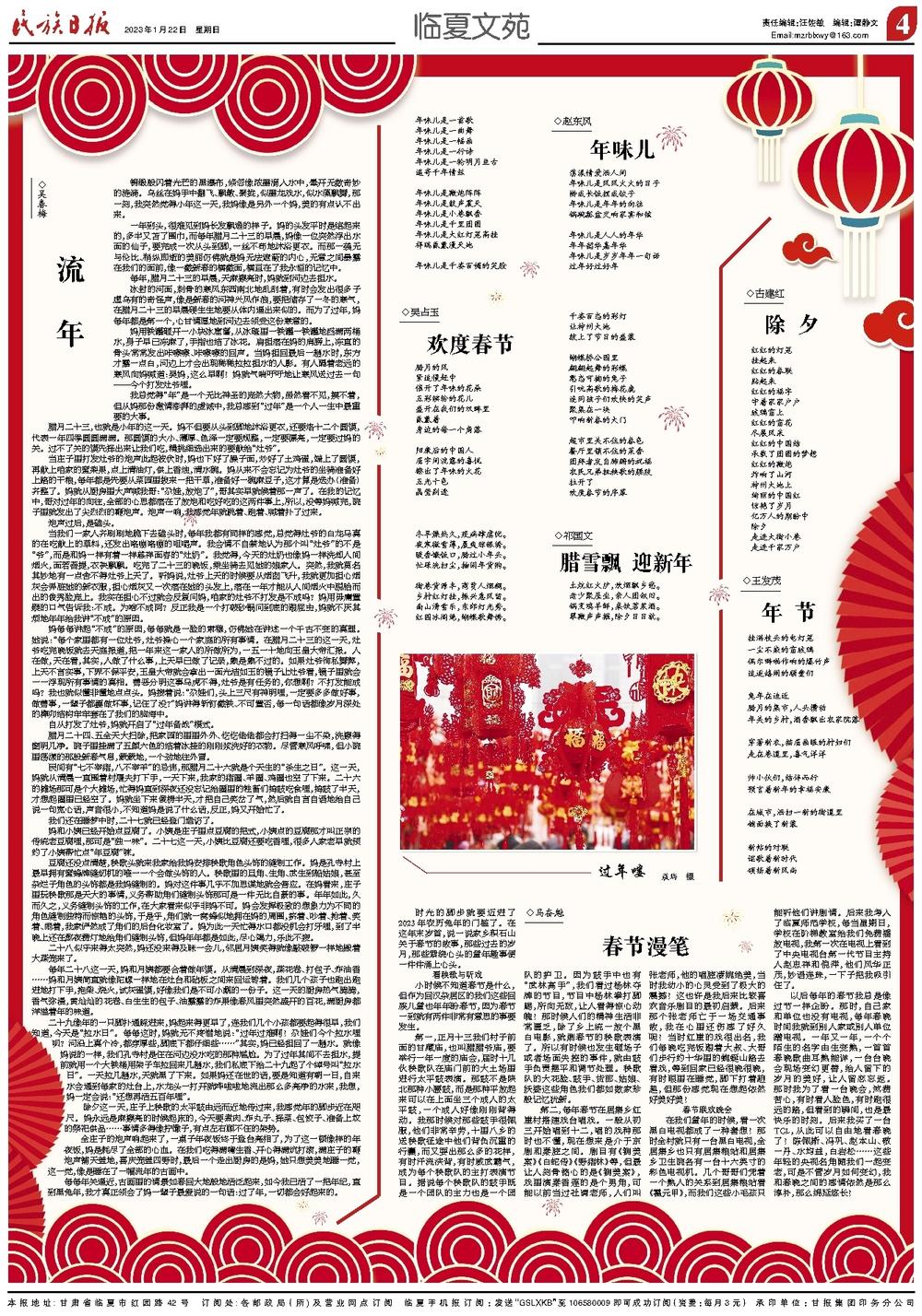◇吴春梅
锦缎般闪着光芒的黑瀑布,倏忽像浓墨滴入水中,晕开无数奇妙的涟漪。乌丝在妈手中翻飞、飘散、聚拢,似墨龙戏水,似水藻飘舞,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小年这一天,我妈像是另外一个妈,美的有点认不出来。
一年到头,很难见到妈长发飘逸的样子。妈的头发平时是绾起来的,多半又苫了围巾,而每年腊月二十三的早晨,妈像一位突然浮出水面的仙子,要完成一次从头到脚,一丝不苟地沐浴更衣。而那一袭无与伦比、稍纵即逝的美丽仿佛就是妈无法遮蔽的内心,无意之间暴露在我们的面前,像一截新春的横截面,横亘在了我永恒的记忆中。
每年,腊月二十三的早晨,天麻擦亮时,妈就到河边去担水。
冰封的河面,刺骨的寒风东西南北地乱刮着,有时会发出很多子虚乌有的奇怪声,像是新春的河神兴风作浪,要把储存了一冬的寒气,在腊月二十三的早晨硬生生地要从体内逼出来似的。而为了过年,妈每年都是第一个,心甘情愿地到河边去领受这份寒意的。
妈用铁罐砸开一小块冰窟窿,从冰碴里一铁罐一铁罐地舀满两桶水,身子早已冻麻了,手指也结了冰花。扁担落在妈的肩膀上,冻直的骨头常常发出咔嚓嚓、咔嚓嚓的回声。当妈担回最后一趟水时,东方才露一点白,河边上才会出现稀稀拉拉担水的人影。有人隔着老远的寒风向妈喊道:吴妈,这么早啊!妈就气喘吁吁地让寒风送过去一句——今个打发灶爷哩。
我总觉得“年”是一个无比神圣的庞然大物,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从妈那份激情澎湃的虔诚中,我总感到“过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
腊月二十三,也就是小年的这一天。妈不但要从头到脚地沐浴更衣,还要烙十二个圆馍,代表一年四季圆圆满满。那圆馍的大小、薄厚、色泽一定要规整,一定要漂亮,一定要过妈的关。过不了关的馍先择出来让我们吃,精挑细选出来的要献给“灶爷”。
当庄子里打发灶爷的炮声此起彼伏时,妈也下好了臊子面,炒好了土鸡蛋,端上了圆馍,再献上咱家的蜜梨果,点上清油灯,供上香烛,清水碗。妈从来不会忘记为灶爷的坐骑准备好上路的干粮,每年都是先要从菜园里拔来一把干草,准备好一碗麻豆子,这才算是迭办(准备)齐整了。妈就从厨房里大声喊我哥:“尕娃,放炮了”,哥其实早就候着那一声了。在我的记忆中,哥对过年的向往,全部的心思都落在了放炮和吃好吃的这两件事上,所以,没等妈喊完,院子里就发出了尖烈烈的鞭炮声。炮声一响,我感觉年就跳着、跑着、喊着扑了过来。
炮声过后,是磕头。
当我们一家人齐刷刷地跪下去磕头时,每年我都有同样的感觉,总觉得灶爷的白龙马真的在吃献上的草料,还发出咯嘣咯嘣的咀嚼声。我会情不自禁地认为那个叫“灶爷”的不是“爷”,而是和妈一样有着一样慈祥面容的“灶奶”。我觉得,今天的灶奶也像妈一样洗却人间烟火,面若菩提,衣袂飘飘。吃完了二十三的晚饭,乘坐骑去见她的娘家人。突然,我就莫名其妙地有一点舍不得灶爷上天了。听妈说,灶爷上天的时候要从烟囱飞升,我就更加担心烟灰会弄脏她的新衣服,担心烟灰又一次落在她的头发上,落在一年才能从人间烟火中脱胎而出的俊秀脸庞上。我实在担心不过就会反复问妈,咱家的灶爷不打发是不成吗?妈用毋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不成。为啥不成阿?反正我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跟屁虫,妈就不厌其烦地年年给我讲“不成”的原因。
妈每每讲起“不成”的原因,每每就是一脸的肃穆,仿佛她在讲述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她说:“每个家里都有一位灶爷,灶爷操心一个家庭的所有事情。在腊月二十三的这一天,灶爷吃完晚饭就去天庭报道,把一年来这一家人的所做所为,一五一十地向玉皇大帝汇报。人在做,天在看,其实,人做了什么事,上天早已做了记录,赖是赖不过的。如果灶爷徇私舞弊,上天不言实事,下界不保平安,玉皇大帝就会拿出一面光洁如玉的镜子让灶爷看,镜子里就会一一浮现所有事情的真相。善恶分明这事马虎不得,灶爷是有任务的,你想啊?不打发能成吗?我也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妈接着说:“尕娃们,头上三尺有神明哩,一定要多多做好事,做善事,一辈子都嫑做坏事,记住了没?”妈讲得斩钉截铁、不可置否,每一句话都像岁月深处的榫卯结构牢牢套在了我们的脑海中。
自从打发了灶爷,妈就开启了“过年备战”模式。
腊月二十四、五全天大扫除,把家园的里里外外、仡仡佬佬都会打扫得一尘不染,洗擦得窗明几净。院子里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结着冰挂的刚刚浆洗好的衣物。尽管寒风呼啸,但小院里荡漾的那股新春气息,簌簌地,一个劲地往外冒。
民间有“七不宰猪,八不宰羊”的忌讳,那腊月二十六就是个天生的“杀生之日”。这一天,妈就从清晨一直围着村屠夫打下手,一天下来,我家的猪圈、羊圈、鸡圈也空了下来。二十六的摊场那可是个大摊场,忙得妈直到深夜还没忘记给圈里的牲畜们捣鼓吃食哩,捣鼓了半天,才想起圈里已经空了。妈就坐下来傻楞半天,才把自己笑岔了气,然后就自言自语地给自己说一句宽心话,声音很小,不知道妈是说了什么话,反正,妈又开始忙了。
我们还在睡梦中时,二十七就已经登门造访了。
妈和小姨已经开始点豆腐了。小姨是庄子里点豆腐的把式,小姨点的豆腐那才叫正宗的传统老豆腐哩,那可是“独一味”。二十七这一天,小姨比豆腐还要吃香哩,很多人家老早就预约了小姨帮忙点“年豆腐”唻。
豆腐还没点清楚,秧歌头就来我家给我妈安排秧歌角色头饰的缝制工作。妈是孔寺村上最早拥有蜜蜂牌缝纫机的唯一一个会做头饰的人。秧歌里的旦角、生角、武生到船姑娘,甚至杂烂子角色的头饰都是我妈缝制的。妈对这件事几乎不加思谋地就会答应。在妈看来,庄子里玩秧歌那是天大的事情,义务帮助角们缝制头饰那可是一件无比自豪的事。年年如此,久而久之,义务缝制头饰的工作,在大家看来似乎非妈不可。妈会发挥极致的想象力为不同的角色缝制独特而惊艳的头饰,于是乎,角们就一窝蜂似地拥在妈的周围,挤着、吵着、抢着、笑着、闹着,我家俨然成了角们的后台化妆室了。妈为此一天忙得水口都没机会打牙哩,到了半晚上还在熬夜费灯地给角们缝制头饰,但妈年年都是如此,尽心竭力,乐此不疲。
二十八似乎来得太突然,妈还没来得及眯一会儿,邻居月姨笑得就像敲破锣一样地搬着大蒸笼来了。
每年二十八这一天,妈和月姨都要合着做年馍。从清晨到深夜,蒸花卷、打包子、炸油香……妈和月姨简直就像陀螺一样地在灶台和砧板之间来回运转着。我们几个孩子也跑出跑进地打下手,抱柴、烧火,试灰蛋馍,好像我们是不可小觑的一份子。这一天的厨房热气腾腾,香气弥漫,黄灿灿的花卷、白生生的包子、油露露的炸果像春风里突然盛开的百花,满厨房都洋溢着年的味道。
二十九像年的一只脚扑通踩进来,妈起来得更早了,连我们几个小孩都要起得很早,我们知道,今天是“拉水日”。每每这时,妈就无不疼惜地说:“过年过难啊!尕娃们今个拉水哩呗?河沿上真个冷,都穿厚些,脚底下都仔细些……”其实,妈已经担回了一趟水。就像妈说的一样,我们孔寺村是住在河边没水吃的那种尴尬。为了过年其间不去担水,提前就用一个大铁桶用架子车拉回来几趟水,我们私底下给二十九起了个绰号叫“拉水日”。一天拉几趟水,天就黑了下来。如果妈还在世的话,要是知道有朝一日,自来水会通到每家的灶台上,水龙头一打开就哗啦啦地流出那么多亮净的水来,我想,妈一定会说:“还想再活五百年哩”。
除夕这一天,庄子上秧歌的太平鼓由远而近地传过来,我感觉年的脚步近在咫尺。妈永远是麻擦亮的时候起床的,今天要煮肉、炸丸子、择菜、包饺子、准备上坟的祭祀供品……事情多得像拧馓子,有点左右顾不住的架势。
全庄子的炮声响起来了,一桌子年夜饭终于登台亮相了,为了这一顿像样的年夜饭,妈是耗尽了全部的心血。在我们吃得满嘴生香、开心得满炕打滚,满庄子的鞭炮声铺天盖地,喜庆笼盖四野时,最后一个走出厨房的是妈,她只想美美地睡一觉,这一觉,像是睡在了一幅流年的古画中。
每每年关逼近,古画里的情景如春回大地般地活泛起来,如今我已活了一把年纪,直到黑兔年,我才真正领会了妈一辈子最爱说的一句话:过了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