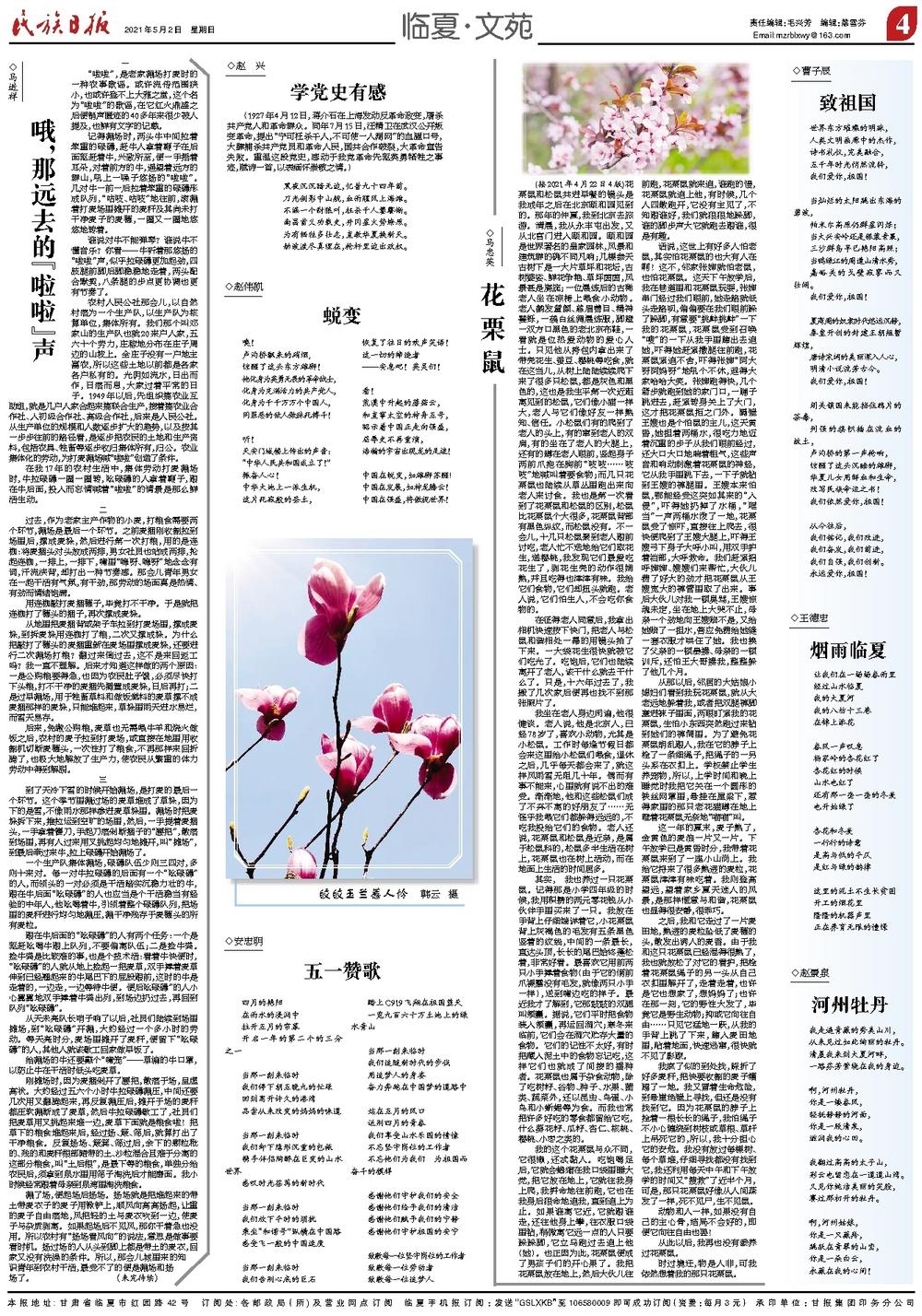◇马进祥
一
“啦啦”,是老家碾场打麦时的一种农事歌谣。或许流传范围狭小,也或许登不上大雅之堂,这个名为“啦啦”的歌谣,在它红火鼎盛之后便销声匿迹的40多年来很少被人提及,也鲜有文字的记载。
记得碾场时,两头牛中间拉着笨重的碌碡,赶牛人拿着鞭子在后面驱赶着牛,兴致所至,便一手捂着耳朵,对着前方的牛,遥望着远方的群山,吼上一嗓子悠扬的“啦啦”。几对牛一前一后拉着笨重的碌碡形成队列,“咕吱、咕吱”地往前,滚碾着打麦场里摊开的麦秆及其尚未打干净麦子的麦穗,一圈又一圈地悠悠地转着。
谁说对牛不能弹琴?谁说牛不懂音乐?你看——牛听着那悠扬的“啦啦”声,似乎拉碌碡更加起劲,四肢腿前脚后脚稳稳地走着,两头配合默契,八条腿的步点更协调也更有节奏了。
农村人民公社那会儿,以自然村落为一个生产队,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集体所有。我们那个叫邓家山的生产队也就20来户人家,五六十个劳力,庄稼地分布在庄子周边的山坡上。全庄子没有一户地主富农,所以这些土地以前都是各家各户私有的。光阴如流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过着平常的日子。1949年以后,先组织搞农业互助组,就是几户人家合起来搞联合生产,接着搞农业合作社、入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后来是人民公社。从生产单位的规模和人数逐步扩大的趋势,以及按其一步步往前的路径看,是逐步把农民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包括农具、牲畜等逐步收归集体所有,归公。农业集体化的劳动,为打麦碾场喊“啦啦”创造了条件。
在我17年的农村生活中,集体劳动打麦碾场时,牛拉碌碡一圈一圈转,吆碌碡的人拿着鞭子,跟在牛后面,投入而忘情喊着“啦啦”的情景是那么鲜活生动。
二
过去,作为老家主产作物的小麦,打粮食需要两个环节,碾场是最后一个环节。之前麦捆刚收割拉到场里后,摞成麦垛,然后进行第一次打粮,用的是连枷:将麦捆头对头放成两排,男女社员也站成两排,抡起连枷,一排上,一排下,嘴里“嗨呀、嗨呀”地念念有词,汗流浃背,却打出一种节奏感。那会儿青年男女在一起干活有气氛,有干劲,那劳动的场面真是热情、有劲而情绪饱满。
用连枷敲打麦捆穗子,毕竟打不干净。于是就把连枷打了穗头的捆子,再次摞成麦垛。
从地里把麦捆背或架子车拉到打麦场里,摞成麦垛,到拆麦垛用连枷打了粮,二次又摞成垛。为什么把敲打了穗头的麦捆重新在麦场里摞成麦垛,还要进行二次碾场打粮?翻过来倒过去,这不是来回返工吗?我一直不理解。后来才知道这样做的两个原因:一是公购粮要得急,也因为农民肚子饿,必须尽快打下头粮,打不干净的麦捆先搁置成麦垛,日后再打;二是过早碾场,用于牲畜草料和做饭燃料的麦草摞不成麦捆那样的麦垛,只能堆起来,草垛里雨天进水易烂,而雪天易存。
后来,免缴公购粮,麦草也无需喂牛羊和烧火做饭之后,农村的麦子拉到打麦场,或直接在地里用收割机切断麦穗头,一次性打了粮食,不再那样来回折腾了,也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得到解脱。
三
到了天冷下雪的时候开始碾场,是打麦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个季节里碾过场的麦草堆成了草垛,因为下的是雪,不像雨水那样渗进麦草垛里。碾场时把麦垛拆下来,推拉运到空旷的场里,然后,一手提着麦捆头,一手拿着镰刀,手起刀落剁断捆子的“腰把”,散落到场里,再有人过来用叉挑起均匀地摊开,叫“摊场”,到最后牵过来牛,拉上碌碡开始碾场了。
一个生产队集体碾场,碌碡队伍少则三四对,多则十来对。每一对牛拉碌碡的后面有一个“吆碌碡”的人,而领头的一对必须是干活踏实沉稳力壮的牛,跟在牛后面“吆碌碡”的人也应当是个干活稳当有经验的中年人,他吆喝着牛,引领着整个碌碡队列,把场里的麦秆进行均匀地碾压,碾干净残存于麦穗头的所有麦粒。
跟在牛后面的“吆碌碡”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驱赶吆喝牛跟上队列,不要偏离队伍;二是捡牛粪。捡牛粪是比较难的事,也是个技术活:看着牛快便时,“吆碌碡”的人就从地上捡起一把麦草,双手捧着麦草伸到已经翘起来的牛尾巴下的屁股跟前,这时的牛是走着的,一边走,一边等待牛便。便后吆碌碡”的人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牛粪出列,到场边扔过去,再回到队列“吆碌碡”。
从天未亮队长哨子响了以后,社员们陆续到场里摊场,到“吆碌碡”开碾,大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劳动。等天亮时分,麦场里摊开了麦秆,便留下“吆碌碡”的人,其他人就该歇工回家做早饭了。
给碾场的牛还要戴个“嘴笼”——草编的牛口罩,以防止牛在干活时低头吃麦草。
刚摊场时,因为麦捆剁开了腰把,散落于场,呈虚高状。大约经过五六个小时牛拉碌碡碾压,中间还要几次用叉翻腾起来,再反复碾压后,摊开于场的麦秆都压软碾断成了麦草,然后牛拉碌碡歇工了,社员们把麦草用叉挑起来堆一边,麦草下面就是粮食啦!把草下的粮食堆起来后,经过扬、簸、筛后,就算打出了干净粮食。反复扬场、簸箕、筛过后,余下的颗粒秕的、残的和麦秆根部随带的土、沙粒混合且难于分离的这部分粮食,叫“土后根”,是最下等的粮食,单独分给农民后,须拿到泉水里用筛子淘洗后才能磨面。我小时候经常跟着母亲到泉湾里淘洗粮食。
碾了场,便起场后扬场。扬场就是把堆起来的带土带麦衣子的麦子用锨铲上,顺风向高高扬起,让重的麦子自由落地,风把轻的土与麦衣吹到一边,使麦子与杂质剥离。如果起场后不见风,那你干着急也没用。所以农村有“扬场看风向”的说法,意思是做事要看时机。扬过场的人从头到脚上都是带土的麦衣,回家又没有洗澡的条件。所以,那会儿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干活,最受不了的便是碾场和扬场了。 (未完待续)